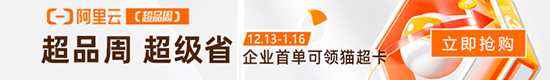五角星的内角和 五角星五个外角之和
还是从我养的一条鱼说起吧,死了,悲伤不已,我不想土葬,我想给它火葬,把鱼灰洒回海洋,让它回到海洋母亲的怀抱,谁知道那玩意儿越烤越香,后来我就买了啤酒,很多事情,初衷并不是那样。
养鱼的故事,在微博上读到的。我还想,这烤鱼如果不放葱花的话,鱼腥味是去不掉的。后来我把烤鱼忘了。等我挪开小美人王嘉惠的小手,烤鱼故事又冒了出来。小美人王嘉惠的指尖冰凉,接住了我鼻尖上流下的雨滴。
本来是她对我的指责,很快成了我对她的报复。因为小美人王嘉惠不说话了,使劲地甩手,直到她抓到了桌上的餐巾纸。她肯定以为是鼻涕。
处理好手上的“鼻涕”,王嘉惠又恢复了对我迟到的责询。
我说我的自行车漏气了。我到高老头那里修车,高老头正在和他老太婆吵架。
小美人王嘉惠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,说,接着给我编。
美人姐姐啊,我一手捂着屁股,一手指头发誓,说谎遭雷劈。
话音未落,外面呼应出了一阵响亮的雷声。雷声还带动了外面的蜂鸣器。很多车辆在雨声中夸张地呼叫。小美人王嘉惠哈哈大笑,说谎!老天爷哪里允许你说谎!高老头刚刚把他老太婆打死了吗?
趁着王嘉惠心情好,我已和王嘉惠的老公周树理同志迅速干了一小杯酒。火热的酒游走在我的身体里。雨声越来越大,高老头渐渐远去,小美人的数落声模糊起来。
五边形的内角之和是540度,五角星的内角之和是180度。我们这个五个死党,可以构成五边形,可以构成五角星。变形的关键在于王嘉惠的老公周树理。如果周树理同志愿意屈尊,我们是五边形。如果周树理同志不愿意,我们就是五角星。周树理是五角星最上面的一个角。谁叫周树理是我们四个人正儿八经的老师呢。但这个老师是有问题的,我们初中毕业不到2年,王嘉惠同学的肚子就大了起来。我们还没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呢,王嘉惠就嫁给了肇事者周树理,升格为我们的师娘。接着我们被邀请参加她和周树理的婚宴,实现了和周树理老师的平起平坐。那场仓促简单的婚宴,就是我们这个五边形或五角星的开始。
更多的时候,我们这个五边形会分裂出一个四边形。四边形的内角之和是360度,小于五边形的内角之和,但绝对大于五角星的五角之和。我、刘永春、周志刚和小美人王嘉惠这四个初中同学常构成稳定的四边形。如果酒多了,小美人王嘉惠则被排斥在外了,刘永春、我、周树理和周志刚会成为斗酒的四边形。王嘉惠也乐得被排斥。三角形也是有的,周树理老师和王嘉惠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如果必须叫王嘉惠一声师娘的话,我、刘永春和周志刚就成了难兄难弟三角形。
但难兄难弟的三角形很少出现,就像很少见到小美人王嘉惠衰老的样子。小美人王嘉惠属于小巧玲珑型,见人一脸笑。以往我们五边形聚会,我也迟到过。王嘉惠并不计较,今天的计较是有理由的,他们要和我们告别了。其实又不是永别,王嘉惠和周树理明天去广州帮忙带孙子。又不是去美国。这不算告别的事,小美人王嘉惠当成了永别,满脸忧戚,与周树理的喜出望外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王嘉惠的数落其实也是诉说忧戚的方式。但女人的话,最好不要上心。她们说话本来就不经过大脑。况且王嘉惠这女人心里敞亮得很,并不是没有主意的人。刘永春和周志刚却上了心,扮演起心灵导师的角色,他们都在往甜处说,往光亮处说。
连喝了四杯酒,我在桌上找开胃的菜。这个饭店的厨师很懒,我的舌尖上全是味精,噎不下去,也吐不出来。
谁能想得周树理也打雷了呢?
周树理打雷的方式是拍桌子!他下手很重,碗筷们也跟着弹跳了起来,颇有当年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气概。
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是周树理老师的名言。当年我们在课堂上讲话声过分了,他就会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,而表达他“不能忍”的方式就是拍讲台。讲台上的粉笔们也跟着他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不过,这样的震摄时间大约五分钟左右。周树理老师师范刚毕业,对付调皮学生的办法还不多。
周老师,你的福气比我们都大,你们都抱孙子的人了,你还有什么“孰不可忍”?
刘永春和周志刚都会意地笑了,就是啊就是啊,我们中间就你们最有福气呢。
王嘉惠头别了过去,抹起了眼泪。
陈小炮!周树理说,你别阴阳怪气好不好?我们明天是去广州帮儿子带孙子,可你们同学偏说她是去为儿子儿媳做狗!
王嘉惠说这话肯定有抱怨辛苦的意思,从某种意义上说,所有的父母都是儿女们的狗呢。可谁能想到周树理竟对“狗”一词那么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呢?
我的面前是好酒。但酒这个东西,喜闹不喜静,越是热闹,它越是如鱼得水。现在如此安静,酒就会拘谨起来,会不安起来。我看到此时此刻的酒在我面前的酒杯里瑟瑟发抖。
安静还是长辈周志刚打破的。他的确是周树理的远房叔叔。长辈起身给我倒了一杯酒,开始了对我的批斗。
今晚发生这么不和谐的事情完全在你陈小炮身上,必须由你陈小炮负全责,如果不是你陈小炮迟到,王嘉惠就不会发火。如果你陈小炮刚才及时把王嘉惠内心的火气消除掉,那么王嘉惠和周树理就不会拌嘴。可你陈小炮为了贪酒,反而跑到桌上大喝特喝。
我也很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我很想说我还酒驾了呢。我很想说我还被王嘉惠踢屁股了呢。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。但我没说我的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为了给我面前的好酒营造一场热烈的氛围,我一定要全身心调动起舌头的积极性。事实上,人只要过了五十岁,不管是内向的,还是外向的。不管是穷人,还是富人,每个人的舌头都有了城府,有了弹性,都会转弯和打结。
我看了看小美人王嘉惠,她还在抹眼泪。我又看了看周树理,他正低着头夹面前的花生米。这花生米有点走油了,吃多了会泻肚。我很想提醒周树理不要多吃。但周树理根本不看我。好吧,周树理老师,既然你对“狗”这个词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,那今晚我偏要给你“脱敏”,给你讲讲狗的故事。
王嘉惠同学,我说,我刚才真没撒谎。我是有个证明的。
刚才我推着自行车去高老头那里打气,高老头真和他老婆吵架。嗓门大得等于在大街上做报告,报告的内容是控诉老太婆的种种不是。老太婆不说话,只是流泪。气筒也摔坏了。老太婆是劝高老头不要修自行车了,和她一起住到苏州女儿女婿家。这样,她也不用两边跑了。高老头说,女儿嫁出去就是人家了。去人家的屋檐下丢人现眼干什么。高老头越说越愤怒,最后说老太婆没用,生不出儿子,只能生女儿。
王嘉惠抬起头,似乎对高老头这句重男轻女的话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但她没说话,眼圈红红的。可怜巴巴的,一瞬间老成了小老太婆。
我继续讲高老头。
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会到高老头那里报到。往往高老头还没跟我说上话,他的狗就迎上来。高老头的车摊在十字路口,摊边摆了几条长凳,很多老头会到摊上集合,上午一群,下午一群,晚上的路灯下又是一群,像群沉默的老兽,围观着高老头修自行车。
高老头说他是黑手党,因为手上全是洗不掉的机油。他常常向我反映偷狗贼的事。每隔两三个月,高老头就会说狗又被偷了!两三个月,正是小狗长大的时间,也是狗肉最嫩的时候。闻见狗肉香,神仙也跳樯。
不能吃狗肉的!王嘉惠突然说,我老爸最后“走”的时候,我特地给塞了打狗饼,在人家说,在人间你吃狗几口,到了阴间,狗也要吃你几口的。
那高老头的小狗从哪里来呢?周志刚问。
要捡小狗,去人民公园啊,过去旧社会的教堂附近有个育婴堂,专门收留走投无路人家的小孩。现在,我们的人民公园是小狗的育婴堂,似乎约定俗成了,尤其是套房人家养狗的,小狗生多了,无法养,只有送到人民公园里,人民公园里人多,会有人收养的,这样比扔到垃圾堆上要好些。
所以,高老头养小狗的程序是这样的。从人民公园里去捡小狗,在修车摊前养到半大,接着被偷狗贼偷走。接着高老头再去人民公园拾小狗。就这样循环往复,帮帮帮帮,帮帮帮帮——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……
陈小炮啊陈小炮,你怎么扯到贝多芬了?
刘永春也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了,竟学周树理拍了桌子,你陈小炮你讲的什么够啊,都是些串了种的,不值钱的草狗,我来讲一个纯种狗拉布拉多。
我们这里哪里有纯种的拉布拉多?要不串种,要不就是近亲结婚。
不是我们这个小县城的,是大城市的,刘永春说,退役的军犬,真正的拉布拉多。我要讲的狗不是广州狗,而是在上海狗。相比我们这里的狗,广州的狗可怜。而上海的狗又比广州的狗可怜,没办法,人住的房子还那么紧张,哪里轮到狗住的地方呢?其实,人比狗更可怜,人是想让狗做伴,做人的奴隶,天下哪里有比狗更忠实的奴隶呢?
拉布拉多是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式住宅区里,说是老宅,单价也有10万一平米,退役军犬拉布拉多就生活在一个退居二线的副厅级官员之家。你们不要想到腐败什么的,只是一条拉布拉多,爸爸也是副厅官员是技术干部,常加班和出差,没法陪独生女,后来就为爱狗的孩子搞到一条退役军犬拉布拉多。小名多多。爸爸给多多在北阳台上砌了一个独立卧室,装了空调。多多聪明,到了晚上,不乱叫,白天出门也很温顺。后来,有年夏天,多多不见了。贴广告查探头悬赏,什么法子都用到了,多多就是不见了。有行家说多多发情了,被母狗套走了。也有人说是偷走做狗肉了。一家人不吃不喝了好多天,像是遭了难。案子是在秋天破的。这也跟腐败没什么关系,一个退位的副厅官员,他是去报案了。但他只是失踪了一条狗,又不是人。你们猜猜?为什么能破了这案子?
副厅官员吃狗头的时候……看到了熟悉的眼神……
陈小炮,给我住口!王嘉惠话到腿到,我的屁股又被她狠狠踢了一脚。
在我夸张的呼救声中,刘永春说出了答案。
拉布拉多被冻在了冰柜里。多多是军犬,身体的某个部位嵌上了芯片。退休官员找到当初的军犬提供方,通过卫星定位,找到了已冻在冰柜里的剥了皮的多多,冰柜是一个狗肉贩子的,吃狗肉的旺季是冬天,狗肉冻在冰柜里,等到冬天再出手。
是狗贩子杀了多多吗?王嘉惠问。
不是,是一个老太太!刘永春这次没让大家猜答案,是多多家楼上的一个老太太,她是一个不喜欢狗的人,是她用毒馒头毒死了多多,然后卖给了狗肉贩子。后来公安局还是出面了,狗贩子和老太太都被抓走了。有谱系登记的纯种拉布拉多市值二十五万,盗窃罪哦。所以啊,大城市的狗,值钱;大城市的人,心毒。
人的命,狗的命,都是狗命,喝酒喝酒。周志刚主动干了一杯酒,眼紧紧闭着,似乎被酒辣了。他最近状况不是很好,他的钱全被什么租宝骗进去了。前年王嘉惠给儿子在广州买房付首付,都向我们借了钱,唯独没向周志刚借,家里的钱全在老婆那里。谁能想得到呢,后来都不属于周志刚了。有次讲到这个事,周志刚轻松地说,反正他也不知道,这样也罢。
外面的雨还很大。这季节本来不会下暴雨,但这些年乱了,有暴雨也正常。告别之夜,暴雨的安排是最合理不过的了。
周树理似乎没听到我们讲狗的故事,他在和谁用手机聊天。
不讲狗命了,下面我讲一个鱼命。
刘永春示意周志刚给自己加酒。周志刚颤抖着给刘永春满上了。刘永春仰头喝下,开始讲鱼的故事。
你们都知道的,我曾有条阿拉斯加雪橇犬。
刘永春的头句话就把我们吓了一跳,他什么时候养狗的?还阿拉斯加雪橇狗?
刘永春和老实吝啬的周志刚可不一样。他总是说酒话,说认识什么大人物,说自己马上有笔大生意,做成了大家一起享福。但也没见他发达过一次。我们五边形聚会,只要刘永春喝醉了,必须由周志刚负责送回家。在我们中间,酒量最大的是刘永春,但容易喝醉的也是刘永春。我个子小,扶不动体重超过我一倍的刘永春。周树理是可送的,但有次,刘永春对周树理说,当年他最爱的女生就是小惠,如果不是周树理以权谋私先下手为强,小惠肯定是他刘永春的。对于刘永春的这次半真半假的酒话,周树理表面没生气,但肯定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。
阿拉斯加雪橇犬有点像二哈,刘永春接着说,所以它又叫三傻。这只三傻不是退役军犬,是它还没满月时我带回家的,当儿子一点点喂大的。那天,我准备出门谈生意,我这个傻儿子以为我要出去旅游了,抢在我前面跳上了车,怎么劝它吓唬它,它也不肯下车。因为我和人约定的时间到了,只有带它走。
一路上,傻儿子很听话,看着窗外的风景,满心的喜悦。它是会笑的,当然也会假笑。那天在车上它是真笑。我要去见的是一个庄园主,人称老法师。老法师是我要做生意的老总的导师。我要谈生意,就必须拿下这个老法师,老法师是老总的前厂长,也是老总的伯乐。老法师退隐江湖了,但人脉还在。我和老法师谈得很开心,成了忘年交。和老法师握手告别的时候,我暗想我的财运快要到来了吧。
谁能想得到呢?我把我的傻儿子给忘记了。我的傻儿子犯大错了。
把老法师咬了?王嘉惠焦急地问道。
傻儿子是不会咬人的,它会咬人我哪会把它带出去啊。刘永春长叹一声,说,我的傻儿子是真坑爹,也怪我,根本不知道傻儿子是阿拉斯加雪橇犬,它是会捉鱼的。我和老法师相谈甚欢的时候,傻儿子跳到老法师精心侍候的渔塘,把池塘里的鱼捉光了。全咬死了。水面上白花花一片!我的头脑更是白花花一片!完了,全完了。我母亲去世,我都没这样的感觉。
阿拉斯加雪橇犬怎么会捉鱼?王嘉惠率先咯咯个的笑了起来。
阿拉斯加雪橇犬会捉鱼的。周树理抬起来,拿出手机上刚刚搜到的答案,给大家上起了课:雪橇犬本来就是在北极圈里,它们为爱斯基摩人拉雪橇,食物除了鱼,就是海豹了……
周树理和王嘉惠不一样,周容易生气,不容易消气。王嘉惠是不容易生气,但容易消气。刘永春的本领可真了得。
后来生意做成了吗?
哪里做成了?如果不是我的傻儿子,那笔大生意就做成了。如果做成了,我就去流转块土地,砌四幢房子,我们四家一家一幢,抱团养老。
刘永春说得很认真。但他说得越是认真,我们就越不能当真。
三傻呢?有没有变成冰箱里狗肉?
我把傻儿子送到我老爸哪了。我老爸倒是很喜欢它,也叫它傻儿子。
那你和你老爸不就是兄弟了?王嘉惠笑得更灿烂了。
唉,这年头,能和儿子成兄弟是福气啊,有人想还想不到呢,小惠,你们去广州,周树理老师能和周宇成兄弟,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周树理点了点头,掩饰不住的得意。
周志刚站起来,又给大家斟了一圈酒,连王嘉惠面前的杯子也倒满了。倒完了酒,周志刚把瓶盖慢慢地拧好,又把屁股下的凳子摆正,很端正地坐下,仿佛是当年周树理的课堂上。
我也给大家讲个狗的故事。有一个老板,生意做得还行,喜欢狗。他和其他人养的狗不一药,他养了两条藏獒,价值一百万。一只白的,叫玉狮;一只黑的,叫墨狮。老板常常牵着两只藏獒散步,那派头相当了得。后来,这两只藏獒还是被老板亲自用棍子打死了。一百万块钱没有了。
发神经了?王嘉惠问。
藏獒突然袭击了老板的母亲。老板的母亲守寡多年,还念佛。藏獒死后,母亲很快生病去世了,老板的头发一下子白了,看到老板的人,都说白藏獒的魂寄在了老板的身上了。
白藏獒是冤枉的?王嘉惠又问。
谁也不知道白藏獒还是黑藏獒,周志刚慢吞吞地说,事后有人说黑白两色就不该在同一窝,黑白无常嘛。
妈妈啊,黑白无常!夜里你不要说得这么吓人好不好?
王嘉惠尖叫了一声,向周树理身边靠过去。
刘永春早把属于周志刚掌握的酒瓶抓到了手里。每每到了这个程度,刘永春必醉了,也好,让这个看上去那么老实但会吓人的周志刚负责把这个醉汉送回家吧,说不定他的傻儿子已捉了无数条鱼在等着他呢。一般下暴雨的时候,河里会有很多大鱼从深水区上来呼吸,如果这时候他的傻儿子阿拉斯加雪橇犬跳下河里,会有非凡的收获。
我的自行车不是今天送给高老头修的,修车是昨天的事。昨天为什么修不好,是因为高老头的狗恰好被一辆车撞死了。高老头正抓着那个司机的衣领,司机是个年轻人,胳膊上有刺青,但他似乎是只绵羊,涨红了脸,支支吾吾的,不说赔,也不说不赔。争吵了很长时间,车子后门开了,出来一个矮个子,比我还要矮,但有威严,一看就是当官的。他让高老头把手放下,高老头真把手放下了。他又问高老头,你有没有合法养狗证?高老头被问住了,回过头,指着围观的老头们说,他们可以证明,这条狗是不是我养的?围观的老头们耳朵似乎听不见。没有人点头。高老头又转向我,这个陈主任可以证明。矮个子领导转向了我,陈主任,你是哪个单位的?我被矮个子领导问住了,我仅仅是一个小副科长,并不是什么主任,如果我承认了,万一他是什么大领导,我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呢。矮个子领导又问了我一遍,我也变得支支吾吾的,说自己只是来修自行车的。这个模糊的回答令高老头非常失望,他丢下我,抱起撞死的狗,瘫坐在豪车的前面,像哭儿子一样哭了起来。高老头哭泣的嗓门很怪,声音不大,像一只离开了母亲的小狗。
陈小炮!你是不是要我把吓死才高兴!王嘉惠站起来,想打断我的讲述。但她已无法阻止我的讲述了。
高老头的哭泣大约经过了两分钟,那个矮个子领导对有刺青的司机耳语了一下,刺青司机打开车门,进去摸了一会儿,往高老头的头上砸了几张红票子。高老头不哭了,将散在地上的红票子一一逮到手里。我数了数,五张。高老头又低声哭了一声,将被撞死的狗抱到一边去了,还将狗头靠到自己的脸上,仿佛是在和它亲热。
我的自行车没修成,高老头也没有怪罪我刚才没为他作证,只是说,今天他把眼睛哭坏了,眼睛看不见修了,明天白天修吧,让我明天晚上来取。
所以,刚才我迟到不是因为下雨,而是因为去取自行车。
高老头后来没给你修自行车?!
周树理冒了一句。
修了。今天下午他喝醉了。我去他的修车摊上,修车摊空空荡荡,不是要下雨了嘛,老人们全回家了。我是在修车摊后面的大树下找到了高老头。高老头满嘴酒气,他已记不清我的自行车,甚至他都记不清我是谁。我把我隆重介绍了三遍,他才把我想起来,也把我的自行车想起来了。他没有忘记我的自行车,自行车也修好了,还打足了乔,摆放在马路对面的车棚里。
我扶着跌跌撞撞的高老头过马路,黄昏的时候,车水马龙,但我感到是兵荒马乱。我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扶着年老体衰的老父亲过马路。
谁能想得到呢,我做了一件狗尾续貂的事,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如果我不多嘴问高老头一句,今天就是一个可以抒情可以思亲的美妙黄昏,和今晚送别我们老同学的氛围很搭配。偏偏我多问了一句话。
你问了什么话?
周树理和王嘉惠几乎是异口同声。
我问,高老头啊高老头,那撞死的狗你怎么了?
高老头没有回答我,而是对我打了一个长长的酒嗝,然后嘿嘿笑,嘿嘿笑,那笑容里全是宽容和慈祥。而我的嘴巴里鼻孔里,满是红烧狗肉的味道。
天啊!他居然吃了自己养的狗!
王嘉惠第一个明白了我的意思,她猛然推开周树理的胳膊,附下身子,呕吐起来,汤汤水水,呈线状地从她嘴巴里喷射出来。
嘉惠,嘉惠!周树理轻拍王嘉惠的背部。
装什么大象啊!刘永春白了周树理一眼,说,周树理啊周树理,你又不是头一次搞大了小惠的肚子,你的炮真准啊,小惠又有了,你赶上好时期了,生二胎不用罚款了。
……谁知道那玩意儿越烤越香,后来我就买了啤酒,很多事情,初衷并不是那样。
是的,很多事情的初衷不是这样,五边形的内角之和等于540度。五角星的内角之和等于180度。外面的雨还在下,每一滴落到地上的雨,并不是从天上下来的雨了。小美人并不叫王嘉惠,叫王家会,是周树理老师给她换的名字。所以,那个叫王家会的女同学,并不是眼前这个呕吐不已的王嘉惠。